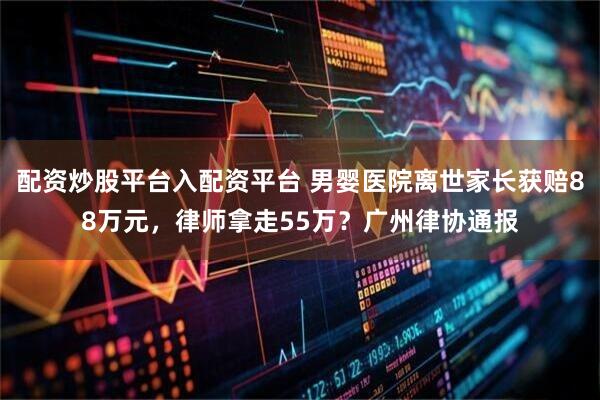在城市的夜幕下,路灯刚亮,广场舞的音响突然响起,“一二一、一二一”声如洪钟般震耳欲聋,陈女士在三楼无奈地关上窗户股票配资怎么赚钱,把孩子的作业移到远离阳台的房间。已经是她这个月第15次被楼下的“暴走团”打扰了。对于不少居民来说,这支“暴走团”的噪音,已经超越了社交的正常范畴,白天到深夜,高分贝的音乐、口号、喇叭声成了让人头痛的“隐形公害”。这种对他人生活空间的噪音侵扰,使得本该是健康的健身活动,成为了邻里之间的“导火线”,引发了越来越强烈的反感。
**一、从早到晚,噪音无处不在**
凌晨五点半,北方某老旧小区依旧沉浸在睡意中,旁边的小广场上却已响起了震耳欲聋的“最炫民族风”。一支40人左右的“暴走团”正绕着广场步伐整齐地走,领队腰间的扩音器音量开到极限,强烈的低音穿透墙壁,钻进了住户的卧室,甚至双层玻璃窗也没能完全隔绝。家住一楼的王大爷患有神经衰弱,每天被这“叫醒服务”弄得失眠,半年多体重下降了十斤。“我不是反对锻炼,可这声音比装修声还刺耳,我们上班族要补觉,老人要安静,为什么就不能放低点音量?”王大爷的抱怨道出了许多居民的心声。
白天公园里的情况也没好到哪里去。南方某城市的湿地公园里,三支“暴走团”在不同区域活动,各自的扩音器放着不同节奏的音乐,为了抢音量,纷纷调高了音量,结果变成了无序的“音量大战”。大学生小林正坐在长椅上看书,戴上降噪耳机,还是能听到隐约的口号声。“原本想找个清静点的地方复习,结果比菜市场还热闹,这哪是公园,简直就是露天迪厅。”
展开剩余71%到了夜晚,“暴走团”的噪音更加令人不安。部分队伍甚至选择在人群密集的街道上活动,扩音器里传出音乐、整齐的步伐声和领队的口号,交织成一种刺耳的音波,在宁静的夜晚格外刺眼。有居民曾测过,经过时的噪音峰值能达到70分贝,相当于吸尘器持续工作时的声音,远超50分贝的夜间噪音限制。这种从清晨到深夜的噪音“全时段覆盖”,让周围居民的生活空间被彻底侵犯。
**二、从公共空间到私人领域,噪音无孔不入**
公共空间的噪音或许还能勉强避开,但一旦“暴走团”的声音侵入到私人领域,矛盾便会爆发。东部某省会城市的滨河小区,紧邻着一条市民散步的步道。最近,一支“暴走团”把步道当作了“训练路线”,每天早晚两次活动,扩音器的音量大得让家里看电视都得调至最大音量,打个电话也得大声嚷嚷。
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,这些噪音还引发了连锁困扰。家住高层的李女士有个刚满一岁的婴儿,每次“暴走团”经过,孩子都会被突如其来的口号声吓醒,哭闹不止。为了让孩子安稳入睡,李女士每天只能在“暴走团”经过的时段,抱着孩子在卧室里来回踱步,“简直像在躲空袭。”一次,她试图下楼与“暴走团”沟通,要求调低音量,却被领队冷冷地回应:“我们锻炼正能量,你家孩子太娇气了!”
学校、医院等需要保持安静的地方,同样未能幸免。中部某城市的儿童医院旁有条本应保持安静的小巷,原本是为了保障患儿休息设置的“静音通道”,却成了“暴走团”的捷径。每天他们的口号和音乐声穿透医院围墙,影响到病房中的小患者。即使医生多次与他们沟通,得到的答复依旧是:“走快点就过去了,不碍事。”这种漠视特殊场所静音需求的行为,显得尤为不合时宜。
**三、从“无意为之”到“理直气壮”,噪音背后的权利错位**
面对“噪音扰民”的投诉,许多“暴走团”的成员总会给出自己的“解释”:“我们声音大是为了整齐步伐,不能散了”“大家一起锻炼是为了图个热闹,声音小了气氛差”“公园广场本来就是公共场所,为什么不能放声歌唱”。这些话的核心,其实是把“个人健身的需求”置于“他人生活安宁权”之上,陷入了“我需要就理所当然”的思维误区。
公共空间的使用从来就不是“谁声音大谁占理”。就像广场舞需要规定音量和时间,夜市要避免过度喧闹一样,“暴走团”的活动也应当遵守“噪音不越界”的基本规则。当扩音器的音量压过居民的交谈声,当口号声打断学生的思考、扰乱病人的休息时,所谓的“健身正能量”早已成了对他人权益的忽视。
每个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之一就是安宁,公共空间的和谐也取决于对“声音边界”的尊重。如果“暴走团”能够将音量调至不干扰他人的范围,或者用手势和哨声代替高分贝的口号,在居民区、学校等场所主动安静一些,也许就能减少许多不必要的冲突。毕竟,健身的真正意义是健康,而健康的社会关系,始终离不开“己所不欲股票配资怎么赚钱,勿施于人”的体谅。当“暴走团”的步伐声不再伴随刺耳的噪音,当集体活动的热闹不再侵占他人的安宁时,或许才真正能够赢得大家的理解,而不是反感。
发布于:山东省信钰证券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